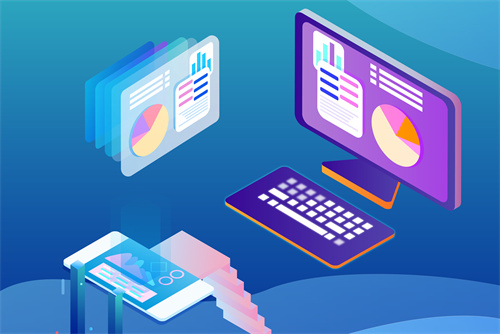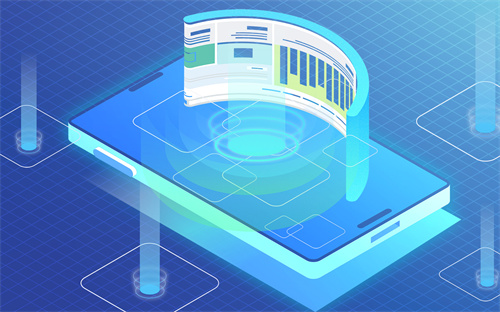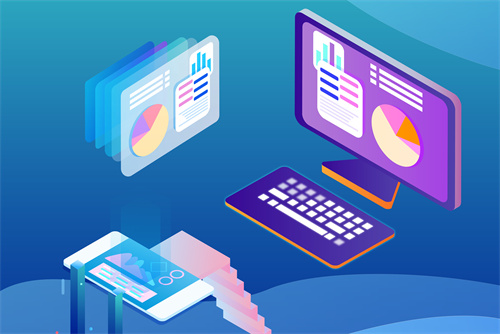谭飞:欢迎张冀兄来到《四味毒叔》。
张冀:谢谢。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谭飞:我现在不好给你加title,就是因为你是个很有名的编剧,大家都知道,那么多作品,这次又是导演,而且我看到署的字幕也是编剧加导演。先讲讲你的第一次转型的心态吧,此时此刻是不是有点像产前抑郁的,因为我问过很多导演,其实要上映前是很紧张的,甚至对每一次评价,风吹草动都特别在意,你此时此刻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张冀:我说实话还行,因为我作为编剧参与的项目比较大。
谭飞:对。
张冀:包括《夺冠》,我认为我经历了《夺冠》,经历了这个,当然这最早之前《中国合伙人》,其实也都是遭遇过一些批评,有一些风波,所以我觉得我经历了这些项目以后呢,我其实心态还是相对比较平和的,当然是有点紧张,但是呢,从我的心里就是我是尽力了,我这次转型做导演更重要的是从情感出发,就是想为家乡拍一个东西。
谭飞:我也看到那封信,写的是情真意切。
张冀:因为我作为个人来讲,我对其实做导演没有那么大野心,我还是一个写故事的人,只是这次不一样,把它拍出来而已。我觉得能拍这个也是我对湖南对长沙有回忆,有情感,这个是支撑我最大的动力。所以整体还好,但是呢你当然面对这么激烈的这个竞争,档期呢这个肯定是有压力的,但我觉得做电影就是要承担这个压力。
谭飞:刚才你也谈到,你的自己内心并不是特别地说,我在意它的票房到底有多高什么的,你是觉得我可能了了一个愿望,那么我想问一个导演对批评和评论的态度,因为我们也知道可能你会面对很多,甚至尖酸刻薄的,有网友的、观众的,你怎么看评论这件事,如果是真诚的评论对你来说,它过于尖锐,你能接受吗?
张冀:就我还好,很正常,现在这个时代不可能有人说你的东西完美,所有人都会喜欢你作品,不会的,这是一个迭代的时代,每个创作者要学会去面对这个批评,因为实际上大家分割得还是比较厉害。年轻人我们也不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特别是今年,特别是这个,包括这个 ChatGPT的时代的到来,你的一点批评真的不重要了。因为可能我现在也人到中年,就是有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吧,我觉得比某一部分批评对我来说可能更重要,比如说你要想,这个东西它出现了,它什么时候替代我呀,它的未来是到底是什么样?对我来说有意思,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人的思维模式,到底面对这个时代你到底要怎么去适应它?比如说我看到年轻人对短视频,是这么地这么去玩它,我当然会焦虑,就是长视频真的会再有一天被短视频替代吗?如果短视频这么发展下去,那是未来真的会有人进电影院吗?对于我来说电影还是传统的,就是在电影院里看的电影才叫电影,但是我认为在年轻人看来已经不是这样了。
谭飞:好,我们说回这部电影,就是可能我是作为一个四川人,就是我内心看完电影以后,可能我会想一个创作者骄傲的或者反映他家乡的电影,怎么样在全国的地域引起共鸣,就是怎么去解决?我说、我表达和我吸收、我想看的这么一个矛盾,对吧?因为可能都看到热爱和骄傲了,但是热爱和骄傲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常态传播,就跟你说的在现代环境下可能这种传播并不是让年轻人特别有感,你是怎么看这两者的差异呢?我很骄傲,我是长沙人,我真的一直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我都看到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骄傲感,但我怎么解决说我可能对这个信息不一定感兴趣,或者说我都没去过长沙,或者说我都不看湖南台节目的,那么一群沉默的,他很可能是大多数的人,怎么去解决这样一个接近性的问题?
张冀:我倒没有骄傲,当然很多湖南人可能因为它的历史和文化会骄傲,我在这个电影里我觉得我也没有想要放进什么骄傲,我就是用一家人,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只是它放在城市的视角去讲,我这一家人他不是从早餐的饭桌出发。
谭飞:对。
张冀:比如说上海屋檐下,它不是这个视角,它是一个城市的4个空间。
谭飞:反而最后的结局是一起吃了个,嗦粉。
张冀:对,他们最后走到一起,所以我认为从家的视角去讲,这个城市这个其实是中国的,我并不认为它就是长沙独有的,这其实很中国。但是当然这个中国这个一家人的这个视角会比以往更大,因为我们现在的城市这个空间是很有意思,我觉得不光是长沙,成都、上海、厦门都是有很多空间的,其实每个空间就代表了某种生活方式和某种生活态度,我选了4个空间。这个书店,而不是夜店,我其实这个方面其实有人跟我提过说,说为什么不从夜店开始,但是我这方面我还比较任性,因为我觉得中国电影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书店了,没有出现书店里的一场谈话。
谭飞:没有出现像廖凡那样的人物。
张冀:对,但我更看重的是他们在书店里的那个书架上后面那些书,因为我也在想可能年轻人,有一部分年轻人吧,他们在小红书、在b站上是谈论哲学的。我其实去年有一段时间在听他们在谈论,其实我还挺惊喜的,就年轻人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传统的打开方式,但有些人年轻人会在夜店,我在长沙永远看到有很多夜店的年轻人,但是我也会看到在书店里深夜在读书的年轻人。我这次更想表现那个书店里的安静的长沙,然后他们出发去在这个城市的网红点打卡,但是对我来讲那个是背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谈话,就是用一场用对话去推动的一场方式,一这种邂逅的方式,其实作为我来讲,可能是必须要有一定的经验和一定的创作时间的作者才会去挑战,就不是说自吹,是因为我其实没有,不太想用把手。
谭飞:其实挺难的。
张冀:对,不太想用把手,不太想用比较高的戏剧化的。
谭飞:因为对你来说,我刚才听的话,是否意味着说你要极致也是肯定没问题,从技术上和你的认知上,但是你不想那么极致,你就想讲你特别想讲的一个故事。
张冀:我觉得极致怎么讲,就是比如说宁浩当时他的疯狂系列,它也是有城市的空间,它也是多线、多人物,它的极致就是快,就是高度的巧合。那个时代是实际上那个年代是一个比较冲的年代。
谭飞:这个词用得挺好。
张冀:对,比较冲,它需要这个文本,需要这种多线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时代,特别是三年疫情以后,是一个疗愈的,实际上是需要一个,我们要缓慢的想一想,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面对什么?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极致,我可能拍书店也是一种极致,我拍对话也是一种极致,我的慢也是一种极致,当然我不敢肯定,甚至我很确定,很多年轻人会不接受这种方式,但是这种极致我觉得它代表了生活。我现在越来越在感兴趣的就是,电影中我到底怎么呈现生活?就是借助一点生活的材料,做一些戏剧上的处理,实际上它很讨便宜。但这次其实我还算比较,我觉得忠实地按照那个生活的节奏去展现,我尽量少用一些戏剧的东西,对我来讲电影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银幕上的生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个人的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时候呈现的?我希望在《长沙夜生活》这部电影里越快越好,越早越好。
谭飞:所以你所有的场景是这种叫融入式的,或者说是很多戏剧的,它有你的发生,其实跟真实几乎一样。好,刚才你讲了几个场景,那么可能也有观众会有遗憾说,我们知道长沙还有很多像打麻将,湖南人爱打麻将,这样的一些,你是否目前的场景还是相对就是比较单维度,是不是没有把长沙更多的大家对它的一个信息量的一个期待完全展现出来?你怎么看这么一个说法?
张冀:其实我有点刻意,我不想拍长沙的洗脚,长沙的麻将,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固有印象的长沙,可能在某种方法上来讲,就是我会刺激一下观众。我知道有部分观众会说你怎么没有麻将,这么local、这么代表性的,那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中国电影这十几年其实 local的画面非常多,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其实在电影中是大量出现的。第二个我还是要从故事出发,就是我这4组人它是构成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最重要的任务不是说他们,其实不是他们漫游长沙,是他们要度过一个孤独的破碎的夜晚。因为在今天这个不普通的夜晚,他们的心事、他们的痛苦都要被展示出来,那最后他们走向和解,就因为那一碗粉,他们坐在一起,嗦那一碗粉,决定向明天出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对这个故事最重要最想去展现的主题,还是从他们的心出发。
谭飞:我甚至有点想到郁达夫的那个《春风沉醉的晚上》。
张冀:《春风沉醉的晚上》。
谭飞:长沙版的现代的《春风沉醉的晚上》的,我倒是也看得出诗意,包括就是这几组人他们在一起,因为有那种天伦的矛盾,但最后解决了,也有当然也会提到说里面有重要的一场戏,就是两人都跳了江,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江,湘江吧应该是。
张冀:湘江,对。
谭飞:但是可能按照物理学的原理,他们跳下去这个这么高,一定会要不然受很大的伤,要不然衣衫破碎,或者至少有一种极其疲惫的神态,但是好像后来两人起来就干净,还一起换了微信这样的处理,是你现在看来是一个bug,还是说你刻意为之,或者说中间有一些其他的镜头怎么没剪进去,为了它的简洁,为了在100分钟内完成叙事,我想听听导演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想法)。
张冀:其实我们在试映阶段已经有观众在提出这个是bug,但是我不想解决这个bug,首先这个行动是浪漫,是非理性,我如果用理性去解决它,可能就得把这个情节完整地删掉,但是呢我最后还是决定保留这个情节。但是如果我一旦要去解释这个情节,对我来说,它就不是浪漫的,我不想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电影还是需要,有时间你不用解释,当然你要承受,比如说观众说我觉得这是有bug看不懂,但我觉得这个引起的讨论和争论,对于我来讲也是有价值的,作为我来讲,我现在就做出了这个选择。
谭飞:其实相当于说你每个电影要给自己留一个跟观众交流的,就是电影也是一个介质,是媒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那么这样的一个介质导致了,就是就算是争议,你都觉得在可以,你的理解或者说你能够接受的范围内。你并不惊讶于这个事,而且你不觉得说我要做到你们心中,我好像把每件事讲得那样的符合所谓的逻辑。
张冀:对我来说,就是那个女孩看到了这个人,他没有走出他的过去,他困在了那个地方,她突然意识到这个男孩从第一分钟跟她讲话,就是在聊这件事,就他因为他前女友落水。他被困在这个城里,长沙对我来讲不是一个网红城市,它是一个其实聊着聊着你就发现它处处埋着生老病死,有很多人的痛苦的城市,那个灯火,那个晚上的灯火,其实照亮的时候这些人是孤单的。那个女孩决定走,决定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她已经有点喜欢上这个男孩了,她想救他,她想拯救。
谭飞:这个方式就是她来拯救他。
张冀:对,她只能想到用一种最极致的方式去救他。
谭飞:湘女多情,这个也认识得到的。
张冀:对,因为这个男孩其实在跟她在湘江有一次很长的一个长镜头,跟她讲嘛讲说,我想我为什么我连救她的一次机会都没有,其实这个女孩听到这句话,她就意识到她只能用一种方式救他,就是让那个男孩真正地去救一次他的前女友,所以其实有点像一场行为艺术。我觉得行为艺术不需要解释,我觉得浪漫不需要解释,如果你解释堂吉诃德为什么要对战风车,它就不是《堂吉诃德》,当然我觉得观众有可以质疑可以不理解的权利。但对于我来讲,就是当一个人决定去救一个人的时候,真正的拯救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浪漫大过任何物理的细节的东西,那个会感动到我,我也取舍过,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浪漫对我来说是我拍这个故事,以及拍这座城市最后的那个精神的东西,当然它也是,我觉得它也是不仅是城市的。
谭飞:当然我们再说到影像,因为编剧转导演其实可能最难的就是影像化的你的剧本,你的文字,你的场景,但是我这次我其实还是蛮欣喜,因为刚才说了,你没有用特别大的广角去展示整个城市,比如灯光、高楼,你还是把它放到一个中景、近景甚至特写,但是其实很不好拍,因为纵深没那么厉害了,对吧?可能好多东西这个窄巷,这个五六层的楼,其实它是电影中比较难解决的,因为它容易给观众造成一种疲劳,或者说会观众会觉得哇没意思。但是我自己看了,我倒觉得对长沙,我作为一个有段时间老去,但最近好多年没去的人,我是觉得它是有滋味的。在影像上张冀导演有什么样的自己的一个设计,因为可能很多编剧转导演第一部在影像上是特别特别难的,有些什么样的准备?包括设计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张冀:我认为编剧转导演最大的难题还是剧本。
谭飞:还是剧本。
张冀:并不是影像,因为编剧知道转导演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他认为他在做编剧的时候被人欺负了。
谭飞:总想那个。
张冀:他总想把他的剧本100%还原,或者说他是封闭的心态。
谭飞:我倒是确实听说过几个人说过这样的话。
张冀:对,拍过拍这个剧本,实际上你最重要的还是要去用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创作,其中就包括这个剧本的创作,因为你要允许演员跟你交流,他如果这句台词说不出来,但我们编剧实际上对这个是很敏感的。
谭飞:还是很在意。
张冀:对,但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比较难破的一个东西,我呢我是因为跟陈可辛导演合作这些年,他对我有一个要求,我开始是很不愿意的,但是我最后还是同意了,就是他每部戏我都必须在现场。其实我就变成他跟演员之间的一个渠道或者桥梁,所以呢我在跟演员交流的时候,我是有一套经验的,因为这些年我就干这个事。
谭飞:是。
张冀:我见的演员包括巩俐、黄渤,当年的张译,实际上这些都是很。
谭飞:很棒的演员。
张冀:很棒的演员,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影像上是这样,首先我懂这个剧本,第二我是爱这个地方,我知道哪个空间,哪种影像能呈现出它生活的质感,实际上我就是要还原它,这决定了我的影像不是切来切去。它相对来说,比如说我们拍那个张婧仪和尹昉那段对话的时候,会有一些长镜头,会有一些那个背景中的灯火,会切到人物细微的一些特写中的表情。我拍这个脱口秀,何岸、张艺兴那一段,其实我就要用相对多的手持去跟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是。
谭飞:他上5楼,还有包括他跟他爸爸在那个围栏里面的一个碰撞。
张冀:对,就是手持,讲他跟那个空间,因为那个空间中有很多镜子,因为张艺兴这个人他实际上他是在追问自己的人,他通过他父亲通过他脱口秀的观众,他要找到自己的人,他是个现代危机意识的这个人物,那这种人物就应该旁边就有一些镜像,比如镜子,比如说一些消防的设备,所以他的影像中就会破碎一点,多一些镜像,多一些手势就很焦虑,这个是张艺兴,然后大排档,我们因为是在室内做了一个比较有怀旧风的这么一个老牌的大排档,一般是双机拍。双机拍这个每一桌,比如说我们有每一桌的食客都有故事,那个老板娘丽姐,就苏岩老师扮演那个丽姐,就穿插于其中,用她的视点去看这个人间烟火,深夜食堂的中国食客。当然这个深夜食堂主要也是拍人的情感,所以我们其实镜头相对比较固定。
谭飞:那么长沙之眼,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他好像跟前面几个有点分隔开,白宇帆他们演的戏也相对偏少,那么这么一个意向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作用在戏里面你觉得?
张冀:我其实从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不想拍得很长沙,它得是长沙,但不能很长沙,今天的长沙已经变了,已经比我小时候。
谭飞:移民城市。
张冀:对,小时候那个时候长沙街头全是长沙话,而且也很辣,就辣得已经不友善了。
谭飞:太辣了。
张冀:对,但是现在它是多元,它是包容,它是年轻的,其实比我那个时候看,我更喜欢今天的长沙,就它能够让一对异乡人在这生活下去,找到家的感觉,所以我是不太想要,我是希望成都人、重庆人、武汉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能反观自己,看到自己跟城市的关系。
谭飞:就是一个所谓二线城市的新一线城市化的过程,必然带来很多的文化的交融、移民甚至对辣的一个调整,我看到你最后切那些东西我觉得肯定比老,因为我知道那个有条街就是长沙的,就特别叫老什么?老奶奶的说法。
张冀:娭毑。
谭飞:老娭毑,那是特别特别辣的,但是现在可能到了现在阶段,它也会有些融合,也没有那么的辣。
张冀:最早的长沙菜没有这么辣,就是我小时候去的长沙就是90年,不,就八九十年代,我少年时候,那个时候是要,因为那个时候快、变,所以它其实就辣到疯狂那个时候。现在呢其实这个城市已经找到某种它的节奏了,其实现在每个城市都在找到自己的节奏,就中国人也在找自己的节奏,我们不是说跟着风潮走,你在找本土的东西,但是又不能沦为本土主义,就是说你什么都local,你还是得有一个打开的视野。所以我特别需要,因为有人建议过我,你就拍一家人,这个观众会觉得这个线索更清晰,仅仅就是一家人嘛,但我为什么我一定要放,这个异乡人这个东西?这一对视角,它可能是支离出去的,但是我就是喜欢他两个陌生的,这两个异乡人,卑微的小镇青年,他们在困在那个摩天轮上,这个城市的烟花也在温暖他们,也在照亮着他们,这个情感大于我要的那个完整性。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从生活本身出发,它提炼出的那个情感和浪漫,反而是我觉得我最坚信这个电影的东西。
谭飞:你刚才也讲到,就是可能你还是有巨大优势转型,因为跟很多大演员合作过,而且也跟很多大导演合作过,你自己知道在现场怎么对那些所谓的有名的演员,当然这次我看到我觉得调度,包括你跟他们的这种交流,从镜头看是非常融洽的啊,甚至我看得到很多二创的东西。那么我最感兴趣是张艺兴的一个发挥,因为他其实整个用在地的语言,他可以很自然自由,因为他本来并不是专业学表演,但是在这个里面演出了一种自然、随意、轻松感,这是我看到的,你怎么评价这几位演员?当然这个婧仪一如既往的稳,尹昉也是能够有一种文艺的质感吧,这几个演员你自己怎么看?
张冀:首先演员你要寻找他,就是他得接近你写的时候这个人物,因为演员确实也都有局限性,就像我们也有局限性,所以要找到确实适合的,婧仪她是湖南人。
谭飞:艺兴也是,纯正的长沙人。
张冀:婧仪她在中学的时候,她在湖南念了6年书,她对长沙是有记忆的,是有体验的,然后呢她其实上演了一些就是偶像剧,什么爱情戏,但我觉得这一次她演的是人生,她不是演单纯演一个偶像剧的关系,她也突破了很多。她第一次在五一广场那天唱歌,当着所有人,其实都是我们没有群演,我们因为那天要实拍,就所有的游客就拿手机拍。
谭飞:他是真的游客在那一起?
张冀:真的游客,她那天非常的紧张,因为她唱歌不是她擅长,那天去出发之前,我就跟她说了一段我跟我父亲的故事,18岁的时候,我跟我父亲第一次逛长沙,就一段这样的故事。其实我写过一封信,在宣传的时候他们也发出来了,我跟她说完那段故事以后她就,可能我有我的方式吧,我对演员我是能体会到的,就是我跟她讲了这段故事,我觉得她也是有感受,她也会想到她的家庭,想到她12岁的时候离开邵阳,一个人来到长沙,她那个东西我们俩是相通的,我们都有跟各自的家庭的关系,跟长沙这座城市共同的回忆,她就冲上去,她就唱。其实我这部戏唯一一次哭就是在监视器看到她,而且我在看那个监视器是一个小监,就是我们是藏在人群后面,我看到这个女孩完全不像一个演员,就像一个回到她12岁,就是背着父母,然后她准备离开那个家的时候那个勇气。
谭飞:就是有很多信息量。
张冀:她嗓子都是有时候都不准,但那个打动,我突然觉得青春很美好,因为我以前都是和比较有经验的女演员合作,像婧仪这种很青春洋溢的演员,我是第一次。我在监视器看,我觉得这个青春真好,不用演,我觉得就是不要演,这个戏就是告诉所有演员不要演,就是把你跟你的情感跟你自己那个,也不叫疼痛吧,就是大家都有感受的东西拿出来,尹昉也是一样,他是会用脑子的演。
谭飞:是,他也挺有技巧,这个演员。
张冀:他是脑子,我是觉得他眼睛。
谭飞:他的眼睛很有信息量。
张冀:我在他第一场戏,我看到他眼睛,我觉得对了,他眼睛有一种很真的东西,就是让我相信的东西,实际上是这个人物。因为这个人物就是因为他太真了,所以他才会变得这么,其实他每天是想死的。
谭飞:其实重度抑郁。
张冀:然后他会每天来到片场上跟我讨论,他是这个戏里比较会跟我讨论的演员,我就跟他对,说你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你为什么要说,他要捋清楚,他实际上他是要一个用理性去找到他表演的逻辑的人,他跟婧仪不一样,婧仪就是冲上去。
谭飞:婧仪的直觉,就是或者叫红尘俗世中的一个青春但是有真心的女子。
张冀:就是她那个飘荡的热浪的空气中,我就说你上了,她就上了。包括我拍那天拍跳河,她开始也很开心,导演我今天第一次吊威亚,但是你知道湘江大桥那个威亚真的吊下去20米高,一上她就哭了。
谭飞:恐高的人吓死了。
张冀:我就说哎呀过一会再放下来吧,其实她已经哭得比较,对,确实很害怕。但是我觉得那两次,比如说第一次当着当众唱歌,第二次在湘江桥把她高高的吊起来,两点钟把她完全吊起来,真的很恐怖,但是这两关一过,我就觉得婧仪我会第二天看就觉得新鲜,就是有那种质感,她来的第一天到她走的那天质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谭飞:她真的留下了人生一段故事在这里,你会觉得不是在演。
张冀:她非常相信那个挑战,她从来没有跟我质疑过,她没有跟我质疑过,她没问为什么我要跳,为什么我跳了以后没有受伤,她没有问。其实跟把她吊起来那一刻,那个东西对她的,因为她知道这件事是不可能的,所以它是抽象的,它是归于另外一个维度的东西,就是两个可怜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告诉这个世界,我们要互相救助。尹昉是这样,尹昉他是他改了一句非常精彩的台词。
谭飞:哪句改了?
张冀:其实我跟他一路在有一些挑战,我改了一次,我改了一次以后,他就说,我觉得他就信任我。演员是这样,你作为导演,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一次机会要让他信任你,让他觉得你可以帮助他,你可以带领他,作为导演带领他完成一个角色,他就会信任。但如果你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就会全程在质疑,质疑他自己,有时候质疑他自己比质疑你更糟糕。
谭飞:不自信。
张冀:对,我跟尹昉就是我们俩聊对白,让对白更好,我们俩就互相信任,就他每次来片场,他就会问这句,我想更好。是这样,他在拍那段他们俩跳桥之前,湘江大桥的对话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总觉得这少了一点什么,我原来台词是,“我其实是不想我每天来这,我每天好像我纠缠在过去,我不能接受现实,我也不是不想接受现实,那我不能接受的到底是什么呢?”他突然来了一句,“我不能接受,接受现实的我自己”,这是他说的。
谭飞:这句特别。
张冀:我就说尹昉就用这句,这句非常,我就说太赞了,那天我看他俩从桥上那段对话,我其实看了很久,我让他拍了很多条,但我其实我觉得第一条就OK了。稍微宽一点的那个,第一条就可以了,那天我真的有点享受,我觉得两个人完全在对话,什么叫对话?就是张婧仪真的在听他讲什么,那个才叫对话,而不是婧仪假装在听,我觉得那天婧仪真的在听,我跟这个小子走了两个小时,突然发现这个人告诉她,一个他生命中最疼痛的一个记忆,那个人有可能是疯的。就这个男孩有可能是疯的,他有可能做出一些出格的事,但这个女孩子我觉得那刻她在听他,所以我那天看了很多遍,就是我觉得终于有一场对话,其实我们在电影中很少看到真正的对话。
谭飞:就是有信息量有意思的或者,能够让观众觉得很舒服,是很少的。
张冀:因为我很不喜欢电影里有些表演,就是他有个人在讲,他也不是真正在讲,有人在听,他也不是真正在听,他只是在演,他们只是在做反应,我就有点受不了。
谭飞:而且他们一起上岸之后,我看隔了5秒,一起并肩走了5秒才说,咱俩留个微信,其实我觉得这个处理我是挺喜欢,就这种留白可能在很多人处理中会剪得更短,但是它就没有仪式感,可能正是这两个青年男女会把这事看得很有仪式感。
张冀:就是生活,就我这个主题就是,我觉得生活就是这个电影追求的终极的那种东西。
谭飞:那来说说艺兴,因为这次完全颠覆了,一个颓废的叫讲长沙话的脱口秀演员,尴聊,大家不笑,最后跟父亲冲突后,他突然讲得很好,他其实一直被父权给压抑了。
张冀:他就是张艺兴,就是我选中他了,我说服他来演我就成功了,他就是张艺兴,张艺兴每天面对的东西就是他要演出,就是他要演出,他要变成一个有说服力的一个演员。
谭飞:而且是一个职业搞演出的。
张冀:对,他要面对这么多观众,他要有说服力,他也有担心。
谭飞:要让别人觉得他红,觉得他有实力,这都是压力。
张冀:他也有担心家庭的质疑,他非常热爱长沙话,他热爱长沙话也就到什么程度,他就跟我讲,我要变成世界上第一个全程用长沙话演一部电影的人。
谭飞:他这次就做到了。
张冀:他的执念,其中我有一句,他在现场过文和友的那个长镜头那一段,他有一句他跟那个女演员对话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普通话。我说艺兴这样,为了完成你这个梦想,我们又去机器跑到厦门,把这句话补录出一句长沙话,就我跟他也是高度吻合,开始我是想,是不是说脱口秀前他讲长沙话,然后他脱口秀就讲普通话,就让这个人物有点变化,就更有变化。
谭飞:可能绝大部分人是这么想的。
张冀:他说我不要,后来他在我们围读的时候,他真的用普通话念了一段,我说不对,当时我就说不要,就讲长沙话。当然我跟艺兴沟通的方式是,艺兴是很有主见的,他知道镜头在哪里,他知道机器怎么运动,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谭飞:他演戏经验还是不少。
张冀:他比我有经验,对。
谭飞:《一出好戏》包括好多剧也演了。
张冀:其实我跟他battle过,就他希望跟他的父亲冲突的时候,会采取一种比如说更轻的方式,但是我坚持。
谭飞:你要头要撞到那里。
张冀:不是,我坚持他父亲要比他强,其实他父亲还在控制他。
谭飞:他父亲压着他。
张冀:就说你要我话没有讲完,他掰他的肩膀,你记不记得这个。
谭飞:我看了。
张冀:其实他父亲要比他强,我告诉他你现在仍然在你的,你事隔多年你以为你已经走出父亲的控制,但是在那个两个男人肉体接触的时候,你仍然感觉到父亲是强过你的,我说这个才是你演这场戏最重要的东西。后来我们俩就讲了40分钟,什么都讲,那40分钟以后我们俩建立了信任,但是可以叫两个人在battle,这个是我跟艺兴的沟通方式。我觉得每个演员我这次都用了一种适合我们之间的沟通方式,我跟苏岩老师其实上就很默契,她是个非常职业的演员,原来我注意到《色戒》《芳华》,她是一个很成熟的演员。
谭飞:她原来演过很多电视剧。
张冀:我们就上来走一遍,然后她如果有一些地方可能稍微不是那么松,不是那么生活化的时候,帮助她破一破。
谭飞:但整体我觉得就是演员在里面的发挥还是各有特色,也会问到,因为第一次当导演,我是听说是完全没有超期、超支,这个对第一次当导演来说,其实是个极大的胜利吧,包括周期这块,我听说甚至是用比较短的时间就。
张冀:实际上跟团队有关,这个团队是我跟陈可辛导演合作十几年。
谭飞:是非常熟。
张冀:完全没有问题。
谭飞:所以我听得出张冀是非常有情商的人,就是因为其实很多编剧他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我觉得你还是一个真正,就是你有同理心,有换位思考能力,这个对调教演员也非常重要。当然也问到现在那最大的一个压力,就是你必须要面对成绩,不管怎么说,你要面对市场的竞争,你怎么看待可能的成绩?你是一个什么心态?
张冀:我在创作阶段我已经考虑观众,但是呢有可能观众现在快到我已经不太能适应,这个有可能,因为我在一年前在创作的时候,我是想着观众,因为我用一家人去聚焦观众的情感。我用亲情、友情、爱情相对我觉得普通人都能get的感情,去形成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城市,以及打破地域的这个情感连接,其实我觉得我都在按照这种方式在做,而且我们相对成本也不高。
谭飞:所以其实压力没那么大。
张冀:是。
谭飞:或者就说,我没有说我给自己一个几个亿小目标什么的,心里是没有的。
张冀:当然我们希望有,因为我以前的作品,编剧作品票房也都还可以。所以我是觉得我这一次还是按照我惯常的,因为我不是写那种,从来不是写强韧性,高戏剧冲突或者高类型的,我一般都是相对比较生活化、情感化。
谭飞:作品都有暖意。
张冀:对,我这次也其实用了我这个优势,但是呢我觉得今年的这个观众的变化,实际上对超出我们的预期。
谭飞:挺大,他的迭代非常快。
张冀:对,这个可能得接受啊得接受,我觉得随着我们这个电影的上映,我们这个片子的独特的优势和价值,也许也会凸显出来。对我来说我做电影从《中国合伙人》开始到现在11年一直在前线创作,经历过很多胜败,我觉得再大的胜或再大的败,它都只是一部电影而已。因为你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你创作者你本身的那个职业生涯,我觉得也不会被一部电影影响,而且我觉得我这部电影,我觉得本质上我还是想真诚地讲一个故事,讲一段情感。
谭飞:那最后一个问题,问问张冀就是第一次尝试之后是不是有瘾了,那今后你的主要的方向是继续做编剧,还是说最好就做导演,或者说还是又编又导,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期待的前景?
张冀:我还是擅长做编剧,我对其实我对做导演没有那么high,可能high一点就是你在跟演员沟通的时候有一点,就是碰撞的时候,但实际上我做编剧的时候也有,所以对我来讲没有那么high。
张冀:当然你面对批评,面对这个创作的挫折,这个是永远存在的,而且现在面对的挫折实际上跟我们刚入行的时候那个挫折是不一样的,传统的故事可能真的要被迭代。
谭飞:你这个话我特别欣赏,因为我觉得现在不是内卷的时候了,就是说你谁跟谁斗谁批评你不重要,你关键是大家一起吸引眼球,让这个行业不再被边缘化,让大家特别年轻人真的是说我会去买票,这才是致命的东西。
张冀:对,就是以前我们80年代的时候,那美国好莱坞他们用大银幕是吧,超大制作让观众走进影院,但现在好莱坞看起来都。
谭飞:他们也解决不了。
张冀:对,那我们怎么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五一档的各个影片都在,其实都在做尝试,如果故事真的在消亡,我觉得这个命题对我来讲可能更迷人吧,即便它是一次失败的,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的设想是一次失败的经历,我也觉得它足够迷人。我其实这段时间有一个感悟吧,我越来越觉得布莱希特那句话,讲得非常符合我现在的这种心境,搞我们这个艺术,搞我们这一行,就宁愿从这个好的,总能从坏的新事物开始,也不要从好的旧事物开始,特别是在这种迭代急剧的情况下,你不去极致尝新。但有可能今天我想的《长沙夜生活》是一种传统的,我当年对电影传统的那种审美做到的某种极致,我拍《长沙夜生活》,就不是拍一个城市宣传片,也不是拍一个。
谭飞:不是文旅,什么推广。
张冀:也不是拍一个文旅或者拍我一个故乡的怀旧片,我其实还是想拍一个中国的故事,就是不同的人能够在这个故事里看到,其实我们走过来是不容易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孤独的心事,那个夜晚中有烟火,也有灯火,这个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不是上天给我们的。但这个创造的东西,我们奋斗的这个东西其实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我们应该一起走下去,我觉得这个故事不是长沙的故事,这也是重庆、成都、武汉,也是今天淄博的故事。
谭飞:淄博烧烤的故事。
张冀:对,就是我们这个烟火和灯火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应该还要坚信这一点。
张冀:有的人会说我的故事开头慢,但是我跟他们说,只有开头慢,可能缓慢一点,你到中后段那个故事才能够慢慢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因为他们是4个空间,4组人物汇聚在慢慢汇聚的时候,交集的时候,你才会有蓬勃感。因为我认为故事还是要先慢慢来,最后才能温汤熬汤,把那锅汤真正熬出来。
谭飞:其实烟火气就是生活的留白。
张冀:长沙这部戏还是,我觉得长沙是有两个,就是两个,一个是烟火,一个是灯火,那个灯火就是家,那个烟火就是这个城市。
谭飞:好的。
张冀:谢谢。
谭飞:谢谢张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