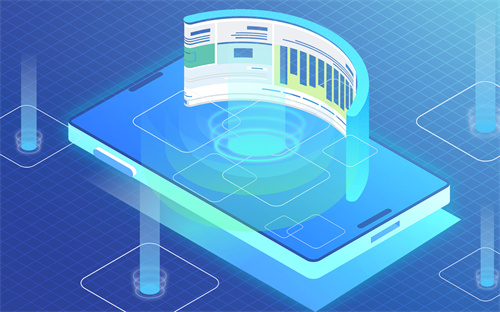谈到“亲密”这个词,我们第一时间反应的,可能是一对关系紧密的恋人,是亲子关系的依恋,是形影不离的女性挚友。却很少出现联想到男性,尤其是两个青春期男性。
这样的反应,是否也是某种社会规训的结果?口碑之作、2022年戛纳金棕榈入围电影,由卢卡斯·德霍特执导的《亲密》,讨论的就是这个议题。
 【资料图】
【资料图】
01.
男女分化,潜移默化地开始了
《亲密》开始时,两位小男孩,雷奥(Léo)和雷米(Rémi)表现得无比亲密,两人在花丛中自由地奔跑,雷奥时常留宿雷米家,甚至成为了雷米妈妈的干儿子,两家家长对男孩们的亲密并未觉得有任何的不妥,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们的自由自在创造了安全的空间。但当他们开始进入学校之后,这种亲密的关系就开始改变了。
无论是雷奥还是雷米,他们其实都很敏感,只不过可能关注的点有些差异:当雷奥进入学校,遭遇女生怀疑他和雷米是不是“一对”(partner)的时候,他便敏锐地意识到了在这个崭新的场域中,他——一个男孩/男人——该扮演的角色,由此而需要展现出的相应的“男性气质”和行为举止。
雷奥需要学习的新课程,便包括该如何正确地与另一个同性相处和交往,尤其当这个同性是你最亲密的朋友时,如何把握其间的距离和分寸。对一个刚刚进入学校这样集体生活的男孩而言,这样的分寸把握远超过他的能力,因此最终他只能选择回避和疏远雷米,最终造成后者的悲剧。
雷奥应该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对于好友雷米的疏远,会带来如此具有毁灭性的后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或许他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对于两个只有13岁的男孩而言,许多事情一方面看似无足轻重,但另一方面,却又似乎已经成为他们未来会成为谁以及该如何生活在这个世上的重要入门必修课。
因为从入学开始,潜移默化的规范、分类和分化便开始了。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说,现代权力运作模式的一个典型特征便是其“毛细血管化”,像教堂、学校、工厂和监狱这些机构,往往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规训的角色,也即阿尔都塞所谓的“意识形态机器”。
在电影《亲密》的学校戏份中,当女孩们询问雷奥和雷米的关系,男孩们对他俩关系充满各种揶揄与暗示时,这个看似仅仅是发生在“无知”少年们间的规训便已经开始运作了,恰恰是这看似不痛不痒的“十目所视”,会形成一种比传统强制性的权力更加丰满、复杂且深入人心的力量。因此,只要雷奥听到各种闲言碎语、看到别人对他们的指指点点,就已经自觉地进入了这一规范系统,并且很快对其内化,最终导致他“自愿”地破坏和雷米的关系。
在《亲密》中,来自学校其他同学们的规训力量首先作用于他们的关系,即需要对于这样一段亲密的同性关系进行界定和命名,所以发生在女孩们和雷奥之间的那段对话,泄露了现代性别制度、亲密关系和身份认同的最大问题。
首先,女孩们根据雷奥和雷米的形影不离与亲密判断他们是“一对”,在她们看来,“亲密的男性关系=同性恋”;雷奥则对此表示反对,他说“那为什么女孩之间也可以很亲密,(却不会被怀疑为同性恋)?”
这一对立背后,便是伊芙·塞吉维克在专著《男人之间》中指出的,现代社会里传统男性同性社交(homosocial)中存在的连续体被打断,从而导致原本流线一样的关系,如今被分割成一段段边界分明的类型——朋友、兄弟、情人等。而伴随着恐同(homophobia)被插入其中,就导致现代男性关系始终处于一种非此即彼的极端状态,从而抹除了其间可能存在的模糊性。
在和女孩们的争执中,雷奥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即他该如何界定自己与雷米的亲密关系?是“最好的朋友”?但他们太过亲密,所以女孩们说,是“友情之上”;雷奥说,“像亲兄弟那样”……正是在这不断被细化、被分类的过程中,男性关系被切割,并且棱角分明,容不下半点灰色。
而这也是现代性别制度的产物,个体的性(sex)与性别(gender)可以被不断地分类和界定(这也是19世纪诞生的性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这基础上所形成的关系也必须一一对应,由此才能被现代强调分类的目光识别,而一旦处于暧昧和模糊之中,便会落入边缘和贱斥的位置。
弗洛伊德曾在《性学三论》中讨论现代社会“男女的分化”,其主要背景以及导致这一分化产生的原因主要来自于社会正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并且不仅仅在现代社会,几乎所有文明和文化中对男女分化都有着相应的论述与规范,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且具有历史性的两性气质。
在乔纳森·奈徳·卡茨(Jonathan Ned Katz)的专著 The Invention of Heterosexuality(异性恋的发明)中,他指出现代西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启了一场建构“异性恋”的巨大工程,其中的首要任务是“男女的分化”。
于是便出现了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提出的一个现象,即无论是被看作属于生物性的性(sex),还是社会的性别(gender),它们其实都属于文化的建构,而其中最核心的一个特征便是两者合力所塑造的两性性别气质,一种看似由生物的和生理的特质所决定的男女性别表现形式,并且——就如女性主义学者们普遍指出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
《亲密》中的雷奥和雷米在进入学校这一意识形态机器后,就必然要面对性别制度的规训,从“男性”身份(电影中男孩子们的聚集都围绕着各种球类运动,如足球和冰球)、“男性应该如何表现”(当雷米枕着雷奥的肚子休息时,雷奥两次躲开)、性取向(雷奥极力否认自己是“基佬”),以及在与异性/同性关系中的恰当距离(雷奥远离了雷米,进入另一个同性的、直男的圈子里)等,这些都是“分化”的主要内容。
这一“分化”过程是以一种分类和差异的方式运作的,且这种差异往往具有强烈的等级色彩,由此导致的过程其实应该反过来看,即首先被确定和标记的往往是一系列“变态”和“错误”,然后根据这些行为建构出关于“正常”的边界,按照克里斯蒂娃的观点,贱斥物(the abject)既是“他者”,也是边界,从而回溯性地构建出“分化”的核心内容。
无论是19世纪的性科学,还是“异性恋”的发明,大都是运用相似的逻辑进行关于“正常”的建构。而在雷奥和雷米的关系中,首先被标记的便是“同性恋”这一标签与行为。
02.
男性友谊的消失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现代性别观念都会根据他们的亲密关系来断定他们的性取向。这是现代“异性恋/同性恋”二元结构的必然产物,并且随着这一现代结构逐渐占据霸权位置,而导致传统诸多其他话语和模式渐渐弱化。
福柯晚年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正是西方传统友谊(friendship)的消失,导致同性恋(homosexual)的诞生。
在大卫·霍尔普林(David M. Halperin)的论文集 How to do the History of Homosexuality(如何书写同性恋史)中,这位著名的研究同性恋史的美国学者指出,在西方传统社会存在着诸多关于男性同性关系的前同性恋话语,而他主要把它分为四种,分别是:①阴柔(effeminacy);②男人/男孩之爱(pederasty)或“主动的”肛交行为(“active”sodomy);③友谊(friendship)或男性之爱(male love);④被动性(passivity)或性倒错(inversion)。而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友谊的话语。
在霍尔普林看来,古代西方的男性友谊经过一个根本的变化,即从传统的不平等转向一种平等的、相互依存和互惠的关系。前者的等级制内含着性感(hot),而其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与色情的联系;但随着蒙田式友谊的出现,两个灵魂融为一体的爱恋开始与色欲对立,从而为特权男性创造了一个安全的表达自身情感和爱的话语空间。
随着现代新范式同性恋(homosexual)的出现,传统关于男性同性关系的诸多话语一方面被吸收融合,另一方面也遭到压抑,虽然并未彻底消失,却已经很难成为主流观念。也正因此,雷奥才会遭遇对他和雷米关系命名的危机,电影名为“close”所展现的也恰恰是一种“蒙田式”的“古典友谊”——一种没有性爱的精神性的情感模式。
而现代友谊——尤其是男性同性之间——中的亲密、温柔和情感表达已经渐渐被剥离到“同性爱”中,而如果否认自己是“基佬”却又与其他男性关系亲密,友谊的话语在当下已经难以为其提供合法性。
也恰恰是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在“男女分化”中的一个差异,即雷奥反问女孩,为什么女生之间的亲密可以被接受且往往不会被怀疑成同性恋?导致这一结果的便是现代性别制度对于男女两性气质和形象不同且往往是对立的二元建构——女性是感性、柔弱与情绪化的;男性则是理性、坚强与理智的。
正是这类老生常谈的性别气质导致现代同性恋往往与“女性化”联系在一起,因此也成为威胁主流男性身份和性别气质的“污点”。而在男性群体内部——如康奈尔在《男性气质》中所指出的,也同样存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男性性别气质秩序,而“女性化”和同性恋都处于边缘且遭到打击——
学校的男孩们似乎更加关注雷奥,而很少揶揄雷米,在某种程度上,雷米的阴柔似乎已经被预设为同性恋。所以,雷奥为了证明自己的男性身份和男子气概,一方面要隔断与雷米的亲密关系(因为会被怀疑是同性恋),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地加入“男孩俱乐部”,通过诸如踢足球、打冰球这样的“男性”运动,来证明和补充自己遭到质疑的男性气质(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娘娘腔”)。
03.
忧郁的男性与男性气质
而这样的割裂所造成的危害,在电影中一方面通过雷米的自杀行为来表现,另一方面就是通过雷奥在其后对好朋友的漫长哀悼进行展现。雷米或许同样意识到了同学们对他和雷奥关系的闲言碎语与指指点点,但对他似乎并未产生很大的影响,反而是雷奥对疏远使其难以忍受。
在某种程度上,雷米就是雷奥的另一个自己,是构成他完整的重要“他者”,当雷奥在性别制度的规范下开始疏远雷米,他所做的或许就是自我阉割,即剥离他的身体和存在中被认为是“女性化”的部分。雷米在电影中被表现为一个害羞、内敛、流泪且情绪会崩溃的男孩,也便在主流的性别气质中被置于“女性化”的位置。
他的自杀,或许也就暗示着雷奥的彻底“男性化”,但这一过程却依旧无法一帆风顺,并且对于雷奥而言,“杀掉”自己的“女性化”-亲密朋友,最终带来的只能是无限的哀悼,最终导致他的自我认同(identity)始终处于一种忧郁状态(melancholia)。
这也便是电影后半段的故事,展现着在强制性的“男女分化”中——尤其当男孩进行自我阉割后,他将永远陷入一种因无法哀悼那失去之物/人而陷入无尽的忧郁之中。在弗洛伊德的《哀悼与忧郁》一文中,他通过比较这两者的特征指出了忧郁的特质——从“对象丧失”转变成了“自我丧失”。
在雷米死后,雷奥的哀悼——通过一种正式的、仪式化的形式——其实始终未能完成,即使他参加了雷米的葬礼,但却依旧未能使哀悼完成,原因便在于他“知道他失去了谁,但不知道他在他那里究竟失去了什么”。
雷奥知道雷米的自杀和自己的行为有关,但他却不明白自己的这些行为意味着什么,因此在电影的整个后半段,即使当雷奥处于众人的热闹喧哗之中,但表现他心理的配乐却始终是悲伤而忧郁的。他几乎再没有开心过,而“分化”后的男性气质也反复地阻止他表达和释放这些情感。
美国纪录片《面具之后》关注的是学校里的男孩子们从小被要求和接受的性别化规训,而其中重要一条就是“男人不流泪”,这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他们的情感和情绪表达。
在雷米死后,同学们举办的追思会上,有个小男孩说自己很少因为伤心而流泪,大都因为愤怒才流泪。雷奥通过在冰球场上反复撞墙和跌倒来伤害自己,在摔断手后,医生问他是否疼的时候他突然放声大哭,情节一方面和电影前面雷奥问母亲,雷米自杀时是否很疼有关;另一方面则是雷奥借着疼这一假面来释放内心压抑的情感,对于一个13岁的男孩来说,性别制度的要求是严酷的,但却也总会有裂缝,例如他晚上跑到哥哥床上,说自己想雷米了;或是他跑到雷米家,见雷米的妈妈。
巴特勒在《性别的麻烦》中提出“忧郁的异性恋”概念,即看似自然、主流的异性恋其实始终处于一种“自我丧失”的忧郁结构中,而“同性恋”便是那个丧失的“对象-自我”。
在某种程度上,男性身份和男性气质同样继承着这样的忧郁结构,因为那些遭到切割的“女性气质”无法被哀悼,最终成为男性气质的“鬼影”,对其纠缠不休;而男性气质自身的残缺也导致它永远无法完善,而只能处于一种遗失的悲惨困境中。而这恰恰是电影后半段中雷奥的主要处境和心理状态。
尾声.
雷米的自杀将成为雷奥一生的记忆。13岁的他向雷米的妈妈坦诚,“责任在我,是我的错,是我把他赶走的”。导致雷奥赶走好朋友的那个无形却又十分强势的原因或许看不见摸不着,但对于都进过学校的我们来说,却又可以切身地感知到——
男孩女孩们意识到彼此的不同而开始形成各种小团体,通过排斥、嘲笑和闲言碎语对所有不符合正统规范的男孩女孩进行规训;而对于每一个可能偏离了规范的男孩女孩而言,学校是个残酷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们往往有着毁灭性的破坏力,他们接受与内化了规范且无力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最终一如既往,从而使得危机四伏。
无论是2022年的《亲密》还是2018年的《女孩》,卢卡斯·德霍特的故事始终围绕着现代社会中的边缘个体以及他们的处境,由此展现出这个看似文明、自诩开放的现代社会背后更加严酷和复杂的权力运作以及对个体造成的束缚与伤害。
作为“祛魅”的现代社会,建基在科学方法和逻辑上的清晰性要求,让模糊、灰色地带和中间状态变得日渐难以维系。在电影前半段,描摹的雷奥和雷米之间的亲密(close)本身就是一种弥散且黏连的状态,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性的关系。恰恰是这一现象引起了性别制度,直白地表现为学校中他人或委婉含蓄、或直接的质疑——的警惕与规范。
成为性存在(sexuality)的个体更是受困其中(雷奥的身份和本质被其与雷米的“亲密”——这一在现代被情欲/性化的关系状态——所界定),生命和生活经验也被条缕清晰地划分与切割放进不同的范畴和标签中,但每一次规范都意味着盈余和贱斥物的出现,于是进行新一轮的分化与命名,循环往复,无穷无尽……
那些游离的、还未被命名或是不知该如何认识的“鬼影”,在不断的镇压中,成为无法被哀悼的存在。
雷米的自杀或许会让雷奥在其后的生活中产生对规范权力的意识与批判,其实当他在电影的最后向雷米的妈妈坦白时,反思或许已经开始了,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这些不易察觉的、被内化的意识形态最终会成为个体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一个“染毒”的过程,《亲密》的故事对于我们而言,或许就是一剂“解毒”的良药。